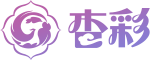动荡的边疆与中国的再造
日期:2026-01-25 13:48:37 / 人气:15

12月的雪后,我在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行驶过枯黄的土地。
这是晋北的一处小路。说是公路,确实比裸露的土路要好一些,但也没有好太多。被轮毂溅起的砂石,不时重重地敲打着车门。路两旁便是冬天的田地,显然长久时间未经打理,只凌乱地戳着某种作物收割后枯败的茎。其余地方便散落着雪,这水的固态潦草地覆盖在土地上,像一种无关的外物,土地裸露的部分未被丝毫浸润,仍然干燥、皲裂。也正在这田间地头里,匍匐着一些新新旧旧的坟茔,站着一些形状特异的树,沉默地标志着死,也宣誓着生。
这片土地带给陌生来客的第一直觉,是苦难。它让人直觉性地畏惧其下深埋的东西:人的骸骨,万物的骸骨,时间的骸骨……最终一切都会变为刚刚超过的那辆运煤车上的、黑色的煤块。抵近这些巨兽时,我意识到它们如此高大,以至于我只能看到它们的轮毂和底盘,它们像激怒的象群,嘶吼着向前冲去。而就在它们的队列里,夹着一辆洋红色的出租车,想必观感是怪异的。就像在看一些80~90年代的电影时,我便不知道那股从头到尾的尘土味道,究竟是来自镜头记录,还是胶片本身。
(卡车,应县,MrQ,2025.12)
为了缓和一下焦躁,我看向后视镜:一座巨型木塔的轮廓,水印般浮现在地平线上,孤独而突兀,让人想起刚才还站在它脚下的震撼。这是近一千年来此地最具标志性的景色。千年前,辽朝二后于此捐建巨构,不纯粹为了礼佛,也希望让南方的宋人知道: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何等能量的对手——建筑在历史上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。我忽而意识到,没错,这里就是千年前的辽宋边界,就是塞外,就是边关。
在这条边界线上,或有兵马粼粼、流民遗泪,也有文人出塞、巨贾入关。如今,来往的身影早不可见了,其中寂寥,只给人一种“中华腹地”的直觉。北国冬日的日落极早,不久,我便见识到暮山之紫——夕色落在山脊上,果真是这样纯粹而奇幻的色彩。古人诚不我欺,我在心里这样感叹。我不明白紫色何以出现,或许是夕光在扬尘里折射了无数次,把“赤橙黄绿青蓝”全都刷掉,最终所剩下的颜色。而这样一想,反倒让我更关心这场仿佛从没停下过的沙尘——北国的空气总是更浑浊一些,像弥漫着粗粝的雾气,你无法抵近它,却无时无刻不在穿越它,它是时间的一部分。
这就是边疆。
(另一处的暮山之紫,大同,MrQ,2025.12)
边疆史是很有意思的学问,但是一个人和边疆要寻一个“缘分到位”的时点。对于我这样久居长三角的人,北魏、辽金,和那个在中原心里遗憾了四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,都是缥缈、边缘的概念。但到了山西,到了大同,当出租车司机跟我很自然地谈起北魏和北齐的时候,我下意识地疑惑:“他怎的如此博学?”。换过角度一想,他所讲述的,大概只是他们耳熟能详的、对“我们从哪里来”这个问题的回答。当我和一位同出身塞外的朋友谈起这个故事时,他颇为感慨地说:我们这里的人,性格中总有一种语言难以表达的沉厚,这就是我们所经历。而我们也因而热爱谈论历史,因为历史像一场随时都能重演的苦难。
我感到:尽管共享一个政治和文化共同体,但南与北的历史叙事仍然迥异。只有到了这片土地,眼见着这片土地的本貌和寄生物,这些历史才终于开始与我有了缘分。在云冈的大佛、应县的高塔下,我开始有动于衷。是为缘起。
(工业文明似乎也带着历史的印记,MrQ,2025.12)
“中心和边缘”是陆地帝国史的经典话题,它们概括了一系列的对立关系:稳定与动态、统治与臣服、主流与少数…对中国而言,也是如此。“边疆”是个不容易讲清楚的话题——它始终是麻烦的根源,却也是活力的来源。而历史的评价,则因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。比如最近关于明清史的诸多争议,实则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“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”(白鲁恂语)在民族国家的时代里面临的挑战:我们应该怎么把“民族”变成一个更包容、非排他的概念?
答案在历史里:中国很特别。很少有陆地帝国是中国这样,困于边疆,却也被边疆持续地重新定义。罗马没有(它与蛮族作战、被蛮族取代),俄罗斯没有(它“内部殖民”了蛮族的土地),奥斯曼也没有(它追求普世主义,但败于民族主义)。这些帝国的统治和被统治是单向的,一旦关系逆转,便走向解体。而中国特别之处是,边疆始终是动态的,双向的。若中原秩序走向崩溃,边疆既是这一进程的关键推手,但也是新的秩序来源。
如果说边界是一条线(这或许是现代地图和民族国家时代才有的概念,在古代,边界或许更是模糊的地带),那么,边疆张力存在于这条线的两侧,哪怕在中原这一侧。在中原秩序出现断裂时,我们更能观测到这种张力,边缘的力量总是在再造中国:比如战国时,最具竞争力的无外乎秦赵两国,对抗异族的最前线并不仅给他们带来的消耗,也有求变的机会。两国活力来自边疆,边疆意味着新的土地、战争资源以及改革的可能。有观点认为,秦处于列国最西,因而能够在新开拓的土地上摆脱分封、实行郡县,是为改革的要素;赵处于最北,胡服骑射的增益自不必说。相比起来,齐虽然占尽了经济地利,却未能在战国后期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。而在秦汉之后,当中原文明陷入第二次断裂时,来自边疆的——如果上一次边疆的活力还只是一种由外而内的“映射”的话,那么这一次,它便是纯粹的外力,鲜卑的北魏整合了北方的秩序,开启了隋的一统和唐的繁荣。
当中心和边缘的力量逆转,历史的主动权往往交给边疆(尤其是北方的边疆)。为何如此?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: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屋顶,北人“出山”易,而南人“入山”难,这也使得华北平原这一中原文明的核心,在地理安全上天然更依附于边疆,这和破碎的南方地理而言,更适合一个统一力量的出现。当然,制度的原因同样重要:南方往往继承了旧秩序的沉疴,比如深陷门阀政治和庄园经济的南朝,而北方的边疆则有新的力量。有趣的是,虽然华北贵为旧文明的中心,但对于那些崛起于边疆的新力量而言,则是新的边疆,这蕴含了的更多冲突和融合的方向。这一点逻辑在地图上不难得到,但是久居南方,是难以有切身体会的。
归根到底,游牧和农耕是按生产方式区划的两类民族,而生产方式必然和组织方式和财富连结在一起,这决定若要跨过二者的分野进行统治,就必须尝试融合两种方式。从社会基础讲,游牧中的个人更多时候游离,而农耕中的个人,则往往生来就在组织和集体当中。这意味着,在成吉思汗将游牧的力量转化为“以战养战”的战争机器前,伟大的建筑工程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,多数时候都是农耕的优势。因而,也不难理解两种文明在经济和财政模式上的区别:游牧文明更亲贸易,也更倾向于向流量的贸易征商税;而农耕文明则倾向于向存量的土地和人口征赋役。因而在社会形态上,游牧的社会气氛(至少在初期)是开放和流动的,而农耕社会则更趋于稳定和保守。这一切换尤其可以从元明之变上看到:在开放但动荡的元朝之后,明朝转向了保守的“洪武体制”。这一政策固然带有明太祖的个人色彩,但也集成了那一代人对于“如何治理”(吸取元末大崩溃教训)的反思。最终,商业的流动和异族的统治一道承受了归咎,遭到了抛弃。
当然,这不是说游牧的社会有多好、治理水平有多高。从历史的结局看,从边疆到中原,从农业到商业,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冲突。对于边缘的新兴力量来说,占据旧文明的核心并不容易:它们都要面临同一个选择:如何固化他们的占有、构筑自身的合法性?在这里,每个看似、正确的选项都有可能通往错误的结局——政治是动态的。同样还是以北魏和元朝为例。
如今令人惊奇的云冈石窟,是北魏平城时代的国家工程,也彰显了佛教作为北魏国家信仰的地位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云冈之肇建,恰在太武帝拓跋焘大力灭佛之后。为何北魏出现了这样一种“急转弯”?或许答案之一,来自北魏政权对中原社会的观察:既然一种外来的信仰能够被一个社会如此普遍地接受,以至于难以根绝,那么外来的统治或许也可以构建于其上。于是在云冈最初的昙曜五窟,用五尊大佛代表五位北魏皇帝,可以被认为是政教的和解,以及相互俘获。不过随后,北魏政权就找到了更直接、稳固的方式:通过“汉化”建构合法性。这成了未来所有入主中原的边疆政权要面临的课题。但汉化这一步走得太快,自然会有问题,核心在于统治集团的分裂。孝文帝选择迁都洛阳来边缘化平城的鲜卑贵族,其与其后人也以对南朝的战争来缓释汉化的压力,那么,一个本就分裂的统治集团,又如何面对帝国内部分崩离析的力量呢?北魏之亡,亦是其内部中心与边缘斗争的结果,来自其内部“边缘力量”的反叛。
(云冈石窟,MrQ, 2025.12)
而轮到蒙古,逻辑是类似的。皇帝们在汉化和蒙古传统的问题上摇摆不决,而“路线之争”又和权力交接等问题(接班是蒙古始终绕不开的制度缺陷)交织在一起,在皇帝频繁更换的元中期,引发制度化进程的频繁回头。而路线的不笃定意味着,元朝既无法像中原王朝那样汲取存量的农耕财富、构建一个稳固(但有周期)的农耕帝国,也无法构建一个依赖商贸流量的游牧帝国,因而表现出来的是“集二者之弊”:既缺乏经济上的动员力,又充满政治上的脆弱性。其90余年的国祚走到最后,不可避免地碎裂为一地各自为战的军阀。
这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清朝,相比以上两代,便颇有些不一样的色彩。不少汉学的研究指向了一种类似“哈布斯堡王朝”的建构,即清朝皇帝头顶汉地、蒙古、中亚的“几顶皇冠”。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,清朝“中心与边缘”的斗争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,其平衡满洲贵族、走向汉化、走向集权的政治路线是确定的,同时也维持了“小财政”,所以到危机来临、支出需求剧增,进一步的汉化、税制改革(关税和厘金)、军事改革都成了其最关键的政治余量。所以,当我们反观充满波折的晚清年代,会发现尽管充斥着各路危机和问题,但它的韧性似乎相当不错。当然,帝国军阀化的结局倒是类似的,这也是王朝末世有限的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——中央为了存续而被迫给出去太多权力,而这种苟延残喘之计,又给未来“收拾旧山河”提供了难度 。
历史的案例展开是收不住的。关于边缘与再造中心的力量,我最直观的感受来自北齐壁画博物馆的一幅壁画:画面中央端坐着不苟言笑的墓主人,仪仗盛大;而在画面的边缘,有一头拥有一双漫画般大眼睛的牛、以及两位欢笑着赶牛的胡人。这是古往今来、中西的画师都爱用的小技巧——将主题置于绘画的中心部分,但把画面的边缘,塑造成趣味和动态细节的游乐场。就像很多人谈论起历史的主题总说:中国在一个个王朝周期中结束后回归原点。远看或许如此,毕竟国家和霸权说到最后,都无非“兴与亡”两个端点而已。但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因周期性而停滞——中国这个文明从来都是忒修斯之船,而它的历史如何,更在于你亲历的方式。你的眼睛,就是有感于过去、震撼于未来的首要窗口。
(壁画边缘的牛,北齐壁画博物馆,MrQ,2025.12)
"
作者:杏彩娱乐注册登录官网
新闻资讯 News
- 陈法蓉直播回应婚育争议:人生没...01-28
- 贝克汉姆家族决裂背后:16亿美元...01-28
- 59岁李若彤近况惊艳!被骗10年倒...01-28
- 前女友实名举报涉毒,何健麒报警...01-28